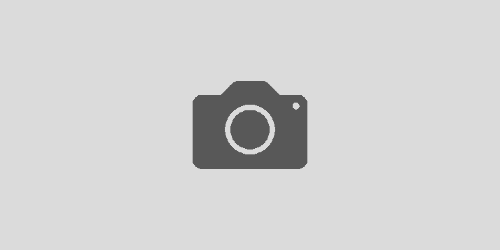战国“夹心饼干”求生实录:韩国的兴亡与吐槽大会
第一章:开局一个碗?不,是开局一场豪赌
历史的牌桌上,总有那么几位玩家,开局就抓了一手烂牌。韩国,无疑就是其中之一。当后世的聚光灯习惯性地投向秦、楚、齐这些“天选之子”时,韩国的身影总显得有些模糊,仿佛是那个在合影时被挤到最后一排,只露出半张脸的同学。
但故事的开端,总要从“想当年”说起。韩国的祖上,也曾阔过。他们是周天子家的“宗亲”,在春秋第一强国——晋国这艘“超级航母”上,也是有头有脸的“高级船员”。到了春秋末期,晋国这艘航母年久失修,公室老板(晋侯)早已被架空,真正掌舵的是以智、赵、魏、韩、范、中行为首的“六大部门经理”,史称“六卿”。
我们的主角韩氏,就是这六大经理之一。只不过,在当时的“经理排行榜”上,韩家实力平平,属于那种开年会时,既不敢坐第一排,也轮不到上台做报告,只能在台下默默鼓掌的角色。
当时晋国的“轮值CEO”,是智氏家族的智伯瑶(又称智襄子)。这位智伯,堪称一位能力与傲慢齐飞的“霸道总裁”。他才华横溢,战功赫赫,但为人却像一瓶没摇匀的可乐,一打开就全是泡沫,呛得人睁不开眼。他的人生信条大概是:“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。”
为了测试自己在“董事会”的权威,智伯发起了一场“强制募捐”:他以辅佐晋侯为名,要求韩、魏、赵三家各献出一百里土地。
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。韩家的掌门人——韩康子,当场就想掀桌子。但他的谋臣段规却悄悄拉住他,耳语道:“智伯这人,又贪又刚愎,不给他,他马上就来打我们。给了他,他就会更膨胀,再去跟别人要。别人不给,他就会去打别人。这样,我们不就可以坐山观虎斗,等待时机了吗?”
韩康子一听,茅塞顿开。这番话翻译成现代职场黑话就是:“老板要作死,千万别拦着,递个梯子让他爬得更高,摔得才惨。”于是,韩康子忍着滴血的心,乖乖地把地交了出去。隔壁的老魏(魏桓子)一看韩家都怂了,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。
土地到手,智伯的自信心爆棚,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。他设下酒宴,邀请韩、魏两家CEO前来“联络感情”。这场饭局,与其说是庆功宴,不如说是智伯的个人霸凌秀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智伯瑶宴饮,而戏康子,又辱其臣段规。” 智伯在酒酣耳热之际,不仅公然戏弄韩康子,还顺带羞辱了他的下属。
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:觥筹交错之间,智伯瑶端着酒杯,用一种近乎施舍的眼神看着韩康子,言语间充满了调侃与轻蔑。韩康子脸上堆着职业的假笑,心里恐怕早已将智伯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遍。那只端着酒杯的手,青筋暴露,却始终没有发作。这一刻的隐忍,是小人物在巨头阴影下的生存本能,也是一场风暴来临前,最压抑的平静。
拿到两块地后,智伯又把目光投向了赵家。赵家的CEO赵襄子是个硬骨头,直接回了两个字:“不给!”
这下可捅了马蜂窝。暴怒的智伯立刻联合韩、魏两家,组成“讨赵联军”,浩浩荡荡地杀向赵家的主城——晋阳。晋阳城高池深,易守难攻,联军围攻了两年多,硬是啃不下来。
久攻不下,智伯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。他发现晋阳城外有条晋水,于是下令筑起大坝,引水灌城。这招釜底抽薪实在太毒辣,没过多久,晋阳城内“巢居而处,悬釜而炊”,百姓们只能在屋顶搭窝,把锅吊起来做饭,眼看就要被“一锅端”了。
胜利在望,智伯彻底飘了。一天,他带着韩康子和魏桓子巡视水坝。看着脚下被洪水围困的孤城,他得意忘形地指着滔滔洪水,对两位“小弟”说了一句堪称史上最经典的“作死名言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对此有生动的记录:“智伯行水,魏桓子为御,韩康子为骖。智伯曰:‘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’”
他说:“哎呀,我今天才知道,原来水也能灭亡一个国家啊!”
话音刚落,韩康子和魏桓子当场脸色煞白,后背的冷汗瞬间浸湿了内衣。他们不是被智伯的“智慧”折服,而是被这句话吓得魂飞魄散。两人迅速进行了一次“脑补”:魏国的都城安邑旁边,有条汾水;韩国的都城平阳旁边,有条绛水。今天你能用水淹赵家,明天是不是就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淹我们两家?
史书记载了当时一个极富电影感的细节:“桓子肘康子,康子履桓子。” 魏桓子不动声色地用胳膊肘碰了碰身边的韩康子,韩康子则心领神会地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面。这一肘一踩,没有一句台词,却胜过千言万语。这套“肢体版摩斯电码”翻译过来就是:“大哥,这孙子留不得了,反了吧!”“妥了,今晚就办!”
当天晚上,赵家的使者张孟谈就潜入了韩、魏两军大营。三方一拍即合,定下了“反杀”剧本:约定日期,赵军从城内杀出,韩、魏两军作为内应,同时决开大堤,让洪水倒灌智伯自己的军营。
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智伯的军队还在做着活捉赵襄子、瓜分赵家的美梦。殊不知,奔涌的晋水已经调转方向,像一头愤怒的巨兽,咆哮着扑向了他们。智氏大军瞬间土崩瓦解,智伯瑶本人也在乱军中被擒杀,不可一世的智氏家族,就此灰飞烟灭。
“晋阳之战”的惊天反转,直接宣告了晋国“六卿时代”的终结。范氏和中行氏早已出局,如今最强的智氏也被团灭,牌桌上只剩下了赵、魏、韩三家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兴高采烈地瓜分智氏留下的庞大遗产。
然而,分蛋糕的时候,现实的骨感再次袭来。
在这场“胜利大联欢”中,三家虽然是平等的合伙人,但分到的“红利”却并不平等。魏国占据了中原大片富庶之地,赵国则向北开拓,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纵深。而我们的主角韩国,分来分去,最后拿到手里的,是夹在秦、魏、楚、赵、郑等一堆强邻之间的一块“四战之地”。
打开战国地图,你会发现韩国的地理位置尴尬到了极点。它没有齐国的沿海之利,没有楚国的广袤腹地,更没有秦国的关中之险。它就像一块被巨石夹在中间的饼干,四面八方都是威胁,出门就可能挨揍,堪称“天生就是困难模式”。这个“C位出道”的地理位置,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韩国在整个战国时期“夹缝求生”的悲催命运。
公元前403年,周天子象征性地发来一纸“营业执照”,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,“三家分晋”尘埃落定,韩国正式挂牌成立。
韩国的诞生,没有开国君主振臂一呼的豪迈,也没有改天换地的革命激情。它更像是一场被逼上梁山的豪赌,赌注是家族的存亡,赌赢的契机,则源于对手的傲慢和自己的隐忍。韩康子用一次教科书级别的“职场背刺”,为韩氏赢得了立国的资本。
然而,这场赌局的胜利,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后遗症——先天不足的地理环境。当开国的香槟泡沫散去,韩王看着地图上自家那块被群狼环伺的“巴掌大”的地盘,恐怕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那么,这家在“新手村”就抽中“地狱难度”的“创业公司”,将如何开启它的下一步呢?是继续在巨头的阴影下瑟瑟发抖,还是会选择“搏一搏,单车变摩托”,去啃一块看似啃不动、却又无比诱人的硬骨头?历史的下一页,早已为它准备好了一场“小鱼吃大鱼”的精彩戏码。
第二章:人生巅峰!吞并一家“百年老店”
在战国初期的“七雄俱乐部”里,韩国就像那个刚通过“人才引进”拿到大城市户口,却住在五环外合租房里的新晋青年。他环顾四周,东边是老牌强国、文化中心齐国;西边是虎狼之秦,正在疯狂健身;北边是刚刚分家的“兄弟”赵、魏,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;南边则是地大物博的“土财主”楚国。
怎么看,这牌局都像是地狱模式。然而,就在韩国的卧榻之侧,还躺着一个看似庞大、实则虚弱的“巨人”——郑国。
说起郑国,那可是“祖上阔过”的典型代表。在春秋时代,它也曾是响当当的“小霸王”,出过像子产那样被孔子点赞的顶级政治家,其国家的商业氛围和法制精神,在当时都是一流水准。可以说,郑国就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、文化底蕴深厚的“老字号”品牌。
然而,时代变了。进入战国这个“一切看肌肉”的时代,郑国这种“文科优等生”就显得格格不入。它沉湎于过去的辉煌,内部公卿内斗不休,国力日渐衰退,就像一位穿着绫罗绸缎、却拄着拐杖还不停咳嗽的贵族老爷,空有架子,里子早就被掏空了。
而新生的韩国,恰恰就是那个觊觎“贵族老爷”家产已久的穷邻居。虽然韩国自身实力有限,但它继承了晋国的一部分军事基因,作风硬朗,充满了“光脚不怕穿鞋的”冲劲。它看着隔壁的郑国,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野狼,看着一只肥硕但年迈的家犬,口水早已流了一地。
韩国对郑国的“并购计划”,并非一时冲动,而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“蚕食”。从韩景侯开始,韩国就利用郑国内乱,不断地出兵“骚扰”,今天占你一个城,明天夺你一个邑,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啄木鸟,一点点地敲碎郑国这棵空心大树的外壳。
这场漫长的“并购拉锯战”,在公元前375年迎来了终局。此时的韩国国君是韩哀侯,他决定不再小打小闹,要对这家“百年老店”进行最后的“资产清算”。
《史记·韩世家》 中的记载极其简洁,却充满了雷霆万钧的力量:“哀侯二年,韩灭郑,因徙都郑。”短短九个字,宣告了一个春秋强国的彻底落幕,也标志着韩国历史达到了它的最高光时刻。
我们可以想象那最后一战的场景。当装备精良、眼神凶狠的韩军攻破新郑城墙时,他们看到的或许不是激烈的巷战,而是一座繁华但迷茫的城市。城里的商人们可能还在计算着今天的盈利,手工业者仍在打磨着精美的器物,而郑国的最后一任国君郑康公,面对着城外的喊杀声,心中涌起的或许不是悲愤,而是一种历史的宿命感。
他也许会想起自己的祖先郑庄公,那位曾在春秋初年“掘地见母”,上演了一出孝感动天大戏的霸主。数百年过去了,郑国的礼乐还在,文化还在,但赖以生存的“铁拳”却早已生锈。当“野蛮”的武力冲垮了“文明”的门槛,一切的诗书礼乐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
这场胜利,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,更像是一场精准的“斩首行动”。韩国用一场赌上国运的总攻,成功地将这家比自己历史更悠久、文化更灿烂的“百年老店”,连同它的“黄金地段”和“无形资产”,一并收入囊中。
灭掉郑国后,韩哀侯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“搬家”!他毫不犹豫地将国都从相对偏僻的阳翟,迁到了地处中原腹地、交通便利、经济发达的新郑。
这次迁都,对韩国而言,无异于一次史诗级的“消费升级”。就好比一家原本在县城开厂的“乡镇企业”,一夜之间并购了位于一线城市CBD的“老字号集团”,并把总部直接搬了过去。
快乐是显而易见的。新郑的繁华,让韩国的国库迅速充盈;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,让韩国的战略地位瞬间提升。韩国终于从一个偏居一隅的“山地国家”,变成了逐鹿中原的“核心玩家”。可以说,吞并郑国,是韩国在战国牌桌上打出的一张王炸,让它短暂地摆脱了“夹心饼干”的窘境,腰杆子都挺直了不少。
然而,烦恼也随之而来。并购一家公司,最难的不是资产交割,而是文化整合。韩国吞并的是一个比自己文化更先进、人心更复杂的郑国。大批郑国的遗民、贵族、士人,一夜之间成了韩国的国民。
这些人,尤其是那些有才华的郑国精英(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申不害,就是郑国人),对韩国这个“征服者”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。他们既可以为韩国所用,成为国家发展的“高级人才”,也可能成为随时会引爆的“定时炸弹”。这就像那家“乡镇企业”虽然住进了豪华的CBD办公室,但发现公司里一半以上都是被并购来的“前朝老臣”,他们说着自己听不太懂的“行业黑话”,遵循着自己不熟悉的“企业文化”,管理起来难度系数极高。
韩国灭郑,是其短暂国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,是一场以小博大、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。它让韩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,也让它第一次尝到了“大国”的滋味。韩哀侯,这位在史书上笔墨不多的君主,也因这场豪赌的胜利,足以在韩国的“功劳簿”上占据一席之地。
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,命运赠送的礼物,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通过武力吞并得来的土地和人口,尤其是消化一个文化上更具优越感的“前浪”,对韩国这个“后浪”的管理智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吃下了郑国这块“大蛋糕”,韩国是会因此消化不良,还是能汲取其精华,让自己脱胎换骨?更重要的是,当一个国家拥有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顶尖人才时,它是否有足够的胸襟和智慧去驾驭他们?下一章,我们将看到,韩国是如何面对这些“甜蜜的烦恼”,并上演一出令人扼腕的“人才悲剧”。
第三章:当“最强大脑”遇到“恋爱脑”老板
如果说吞并郑国是韩国在战国牌桌上打出的一张“王炸”,那么接下来如何出牌,则考验着这家“暴发户”的真正智慧。历史给了韩国一手顶级好牌——它成了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“震源地”,诞生了两位足以改变时代格局的“最强大脑”:一位是申不害,另一位,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,韩非。
申不害的故事我们暂且按下不表,单说韩非。他的存在,让韩国的悲剧色彩,又平添了几分荒诞。一个国家,拥有了能够统一天下的“屠龙之术”,最终却眼睁睁看着这本“武功秘籍”被对手学了去,然后回头一刀,把自己给灭了。这出戏的主角,是“最强大脑”韩非;而导演,则是他那位堪称“恋爱脑”的国君老板。
这里的“恋爱脑”,并非指沉迷情爱,而是一种更致命的症状:在重大决策上缺乏理性,逻辑混乱,感情用事,轻易被身边人(尤其是强者或谗言者)左右,最终做出“坑死自己人,资助竞争对手”的迷惑操作。
韩非,是韩国的王室公子,根正苗红的“官N代”。他师从儒学大师荀子,与后来秦国的丞相李斯是同门师兄弟。可以说,他拿到的,是当时最顶级的“教育资源包”。韩非的智慧,如同一台超高频的处理器,洞悉了战国乱世的终极密码——唯有绝对的法制与君权,才能终结一切纷争。他将商鞅的“法”、申不害的“术”和慎到的“势”融为一炉,写出了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等一系列著作,堪称战国版《君主论》。
然而,命运给这位天才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 记载,韩非“为人口吃,不能道说,而善著书。”
有着“最强大脑”的韩非,在说话上却有致命短板——严重口吃。那是一个靠口才定江山的时代,他就像不会射门的顶级前锋,纵有万策却难以临门一脚。多次上书韩王安而无果,他只能把思想与愤懑写进书中,却意外在诸国高层迅速传播。
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著作时,被那冷酷精准的帝王术深深折服,感叹道:“接乎!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 为了见到这位“技术宅”偶像,嬴政直接南征韩国——逼其派人求和。韩王安慌乱中,派出最懂道理却最不善外交的韩非为使者,等于将“王炸”拱手送给对手。
韩非抵达咸阳,与嬴政相谈甚欢,本可迎来人生转折,却遭同门李斯嫉恨。李斯进谗:“韩非毕竟是韩国宗室,终心向韩,不会真心为秦。” 这击中了嬴政多疑的帝王心,他将韩非下狱。李斯随即送毒药,迫其自尽。
这位未曾施展抱负的“最强大脑”,最终死在自己“粉丝”的牢中,死于同窗的妒恨。韩非之死,也宣告了韩国“人才战略”的终结。
一个连自己国家最顶级的人才都无法识别、无法保护、甚至亲手送入虎口的政权,其未来的命运,已经写在了墙上。
韩非的悲剧,是韩国整体悲剧的一个缩影。这个国家,仿佛一个寓言故事里最愚蠢的主人公,其行为充满了令人费解的反差。
一方面,它拥有韩非这样能够设计出“帝国操作系统”的顶级思想家。韩非的法家理论,就是一部为终结乱世而生的“屠龙之术”,他写下的著作,就是那柄削铁如泥的“屠龙之剑”。而当时的天下大乱,不就是一条亟待被终结的“恶龙”吗?
另一方面,韩国的“硬件”也堪称顶级。“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”,这些精良的武器,就是射穿龙鳞的“破甲之箭”。
然而,故事的走向却滑向了黑色幽默。韩国这位“天选的屠龙者”,自己却根本不敢、也想不到要去屠龙。他觉得那把“屠龙之剑”太重、太锋利,怕伤到自己;他觉得那些“破甲之箭”太珍贵,舍不得用。
当最大、最凶恶的那条龙——秦国,咆哮着来到他家门口时,他非但没有挥剑迎战,反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:他恭恭敬敬地把“屠龙之剑”和一把“破甲之箭”作为礼物,献给了恶龙,谄媚地说道:“龙大爷,这宝贝是孝敬您的,您看能不能别吃我?”
恶龙收下了这份厚礼,满意地打量着这把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神兵,然后,它张开血盆大口,第一个就将这位愚蠢的“献宝者”吞了下去。
手握终结乱世的钥匙,却把它交给了最大的乱世源头。这种荒谬,深刻地揭示了韩国的根本问题:一个国家的强大,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天才和多少利器,而在于它的领导层,是否拥有使用这些天才和利器的智慧与魄力。
韩非之死,宣告了韩国在“人才战争”中的完败。这是一个国家亲手扼杀了自己最后的希望,其过程充满了人性的幽暗——君主的昏聩、同僚的嫉妒、天才的无奈,交织成一曲宿命的悲歌。
当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宝贵的财富——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——都无法转化为国力,反而成了“资敌”的资本时,它的灭亡,就已经不再是“会不会”的问题,而仅仅是“什么时候”的问题了。
既然连送出“最强大脑”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事都干得出来,那么,在亡国的倒计时里,这位“恋爱脑”附体的韩王,还会开出怎样“惊世骇俗”的“救国良方”呢?历史的剧本,永远比小说更离奇。接下来,我们将看到韩国在作死大赛上,又贡献了一个堪称史诗级的“乌龙”操作。
第四章:亡国倒计时:花样作死大赛
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碾过战国七雄最后一个还算太平的清晨,韩国的都城新郑,早已没有了当年“天下之咽喉”的半分豪气。秦国的兵锋,如同一头贪婪的巨兽,在黄河对岸磨砺着爪牙,每一次低沉的咆哮都让韩地风声鹤唳。
此刻,韩国的宫殿里,气氛大概比三九天的冰窖还要凝重。韩王安,这位生不逢时的末代君主,脸色苍白地坐在王位上,眼神空洞地望着下方噤若寒蝉的群臣。这已经不是一场商讨国策的朝会,而更像是一场大型的病危通知家属座谈会。议题千年不变,核心思想只有一个:秦国又生气了,我们该怎么办?
面对这道送命题,韩国的君臣们没有选择奋起反抗,也没有选择同仇敌忾,而是开始了一场惊世骇俗的“花样作死大赛”。他们开出的“药方”,每一个都堪称“脑洞大开”,精准地避开了所有生存的可能,堪称一部亡国教科书。
在所有“治国冥方”中,“疲秦计”无疑是最具黑色幽默色彩的一笔。
故事的开端,是在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里。韩王君臣们经过数个日夜的“头脑风暴”,终于憋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深莫测的“大招”:我们不是打不过秦国吗?那就让他们自己累死!怎么累?派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,去忽悠秦国人,在关中平原上修一条史无前例的巨大水渠。
这个计划的逻辑堪称完美:第一,大型基建耗资巨大,足以掏空秦国国库;第二,工程难度高,工期漫长,可以拖住秦国数十年,使其无力东出。韩国君臣们仿佛已经看到了秦国因为财政赤字而崩溃,人民因为劳役而怨声载道的“美好”未来。
于是,郑国上路了。他凭借出色的专业技术和“忠诚”的表演,成功说服了秦王政。工程上马,举国之力,关中大地尘土飞扬。然而,剧情的发展却完全脱离了韩国人的剧本。秦国强大的国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,硬是把这个韩国人眼中的“豆腐渣工程”和“财政无底洞”,建成了泽被后世的宏伟工程——郑国渠。
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记载了这出间谍大戏颇具讽刺性的一幕。当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时,他非但没有惊慌,反而对秦王说出了那段足以让韩王吐血的实话:
“始臣为间,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臣为韩延数岁之命,而为秦建万世之功。”
翻译过来就是:“没错,我开始是间谍,但现在这水渠修成了,对你们秦国也是大大的好事啊。我这么一折腾,为韩国延续了几年国祚,却也为大秦奠定了万世基业。”
秦王一听,觉得这间谍说得太有道理了,非但没杀他,反而让他继续主持修完了水渠。从此,八百里秦川化为沃野,粮食产量飙升,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最坚实的后勤保障。当秦军士兵吃着郑国渠浇灌出的小米,磨刀霍霍杀向韩国时,不知韩王安的脸上,是何等的五味杂陈。
这堪称间谍史上最失败,也是最成功的案例。韩国想给秦国下毒,结果却亲手为对手配了一碗十全大补汤,把自己补进了坟墓。
如果说“疲秦计”是病急乱投医的荒唐之举,那么韩国末期的“外交”,则是一场凌迟式的集体沉沦。
让我们虚构一位韩国老臣——司地大夫公孙咎。他的主要工作,就是负责与秦国交涉,勘定国界,签署割地条约。
公孙咎第一次奉命去割让上党郡时,他悲愤欲绝。在朝堂上,他声泪俱下,痛陈国土沦丧之耻。前往秦国军营的路上,他一路唉声叹气,仿佛去奔丧。签署条约时,他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,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刻在自己心上。回到新郑,他大病一场,闭门不出,自称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
然而,秦国的胃口是无底的。几年后,秦使又来了,这次点名要的是阳城和负黍。韩王安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公孙咎。这一次,公孙咎只是默默地叹了口气,领命而去。朝堂上的慷慨陈词没有了,路上的悲戚也淡了许多。他只是在交割完毕后,对着故国的山川,多站了一会儿。
再后来,割地成了常态。公孙咎的业务也变得异常熟练。当秦国使者带着地图前来时,他甚至能平静地坐下来,一边喝茶,一边用朱笔在地图上画圈,动作精准而优雅。他会“贴心”地为秦国使者规划出一条最方便接收的路线,详细说明哪里的城防已经松弛,哪里的官仓还有余粮,甚至会提醒对方注意某段路的山贼。
秦国使者都对他“专业”的态度赞不绝口,称其为“识时务者”。而公孙咎的内心,早已从悲愤、无奈,走向了彻底的麻木。他不再感到痛苦,因为痛苦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他看着韩国的疆域在自己手中一寸寸缩小,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裁缝,在裁剪一件注定要被丢弃的破旧衣袍。
这种麻木,正是韩国末期整个国家精神状态的缩影。从君主到大臣,他们不再讨论如何强国,如何抵抗,唯一的议题就是:“报告大王,秦国又来要地了,这次咱们割哪块,才能让他们满意地多宽限几天?”
在慢性死亡的过程中,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本身,而是对死亡的习惯与麻木。
公元前230年,倒计时终于归零。
秦国大将内史腾率领的大军兵临新郑城下。这一次,秦国人连地图都懒得拿了,他们要的是全部。面对黑云压城般的秦军,韩王安没有选择玉石俱焚,甚至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。他非常“识时务”地打开了城门,率领百官,献出王印与国图,选择了投降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对此的记载极为简洁,却字字千钧:
“十七年,内史腾攻韩,得韩王安,尽纳其地,以其地为颍川郡。”
短短数语,一个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国家,就此在地图上被抹去。
起初,秦国对这位亡国之君还算客气。秦王政没有杀他,也没有过分羞辱他,而是将他“妥善安置”在了陈县(今河南淮阳)。这个举动,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似乎给还在苟延残喘的其余五国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:看,投降的待遇还不错,至少能保全性命和一定的体面,这或许是“投降输一半”的最佳范例。一时间,六国旧贵族中,主张妥协投降的声音似乎找到了最有力的论据。
然而,所有人都低估了秦始皇的铁腕与决心。几年后,韩国故地爆发了旧贵族的叛乱,企图复国。消息传到咸阳,秦王政勃然大怒。在他看来,这无疑是对自己权威的挑衅,而留着韩王安,终究是个祸患。
一道冷酷的命令随即下达。公元前226年,韩王安被赐死于流放之地。他的死,像一盆冰水,兜头浇醒了那些还做着“投降输一半”美梦的六国君臣。他们终于明白,在秦国统一天下的铁蹄面前,不存在任何侥幸与妥协。要么在战场上被消灭,要么在投降后被清算,结局并无不同。
韩王安的死,彻底打破了六国旧贵的幻想,也为后来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更加惨烈、更加悲壮的亡国悲剧,拉开了血腥的序幕。
回顾韩国的灭亡之路,从异想天开的“疲秦计”,到麻木不仁的“割地疗法”,再到韩王安天真的“投降求生”,每一步都走得荒腔走板,却又精准地踩在了亡国的鼓点上。他们用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操作,完美演绎了何为“不作死就不会死”。
韩国的悲剧,与其说是亡于强秦,不如说是亡于自身的怯懦、短视和精神沉沦。它用自己的覆灭,为战国末年的大戏贡献了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开幕演出。
那么,目睹了韩国这场“花样作死大赛”全过程的其他六国,他们是否能吸取一二教训,拿出点不一样的应对之策呢?还是说,他们早已买好了下一场大赛的门票,正摩拳擦掌,准备上演更加精彩的作死戏码?历史的答案,往往比戏剧更加残酷,也更加有趣。
第五章:国虽亡,魂不散:一个刺客和一个谋圣的诞生
公元前230年,秦国的军队在将领内史腾的率领下,兵不血刃地开进了韩国都城新郑。史书的记载冰冷而克制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 中只有寥寥数语:“内史腾攻韩,得韩王安,尽纳其地,置以为颍川郡。”
没有惨烈的围城,没有悲壮的殉国。韩国,这个在夹缝中挣扎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国家,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从地图上被抹去了。它的告别,像秋风中的一片落叶,无声,却也彻骨。韩王安被俘,成了六国君主中第一个“下岗再就业”的亡国之君。对于秦国而言,这只是统一大业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;但对于那些故国之人,天,塌了。
故事到这里,似乎应该画上句号。但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,当一扇门被关上时,它往往会为你打开一扇窗,虽然窗外可能正刮着十二级台风。韩国的肉身虽死,但它的“复仇者联盟”,才刚刚上线。
在亡国的韩人中,有一个名叫张良的青年,他的悲愤,比任何人都要深沉。因为他的家族,是韩国最显赫的贵族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 记载,张良的祖父和父亲,曾先后辅佐过五位韩王(“五世相韩”),是名副其实的“国之栋梁”。如今国破家亡,对于张良而言,这不仅是亡国之痛,更是亡家之恨。
这位昔日的贵公子,没有选择在悲伤中沉沦,而是选择了一条最刚烈、也最直接的道路——复仇。他散尽万贯家财,连家里的三百童仆都变卖了,只为寻访能够刺杀秦王的天下奇人。他不是要复国,他是要用最原始的方式,让那个毁灭他家国的罪魁祸首,血债血偿。
终于,他在东海之滨找到了一位大力士。这位力士能抡起一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。在秦代,一斤约等于今天的256克,一百二十斤,就是三十多公斤,约等于一台家用微波炉的重量。张良为这位猛男量身打造了这件“人间凶器”,然后,静静地等待一个机会。
机会很快就来了。秦始皇东巡,车队将经过博浪沙(今河南原阳县境内)。张良与那位大力士,像潜伏的猎豹,埋伏在路边。当那支象征着帝国至高权力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来时,张良算准了秦始皇乘坐的最华丽的那辆车。他一声令下,大力士用尽平生之力,将那柄呼啸的铁锤,如同一颗黑色流星,狠狠地砸了过去!
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 描绘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:“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,误中副车。”
“哐”的一声巨响,地动山摇,车驾被砸得粉碎。然而,结果却是一个巨大的乌龙——他们砸中的,是副车。真正的秦始皇,因为防备刺杀,正安然无恙地坐在另一辆不起眼的车里。
惊天一击,功败垂成。秦始皇当场暴怒,下令“大索天下,求贼甚急”。一张天罗地网在全国铺开,而张良,则开始了亡命天涯的逃亡生涯。此刻的他,是一个失败的刺客,一个愤怒的青年,一个被帝国机器追捕的亡命徒。他用尽全力挥出的一拳,打在了棉花上,除了激起对方的愤怒,一无所获。
博浪沙的失败,对张良而言,是一次痛苦的“格式化”。他意识到,仅凭一腔热血和个人勇武,是无法撼动一个庞大帝国的。在逃亡到下邳(今江苏睢宁)的日子里,他遇到了一个彻底改变他一生的人,也经历了一段堪称“玄幻”的奇遇。
一天,张良在桥上散步,遇到一位穿着粗布衣服的老人。老人走到他面前,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,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:“小子,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!”(“小子,下,取履!”)
张良当时就想发作(“良愕然,欲殴之”),心想我好歹也是个通缉犯,你个老头还敢这么跟我说话?但他看对方年迈,硬是把火气压了下去,默默地到桥下捡回了鞋。谁知,老人得寸进尺,把脚一伸,命令道:“给我穿上!”(“履我!”)
张… …良… …忍… …了。他跪在地上,恭恭敬敬地为老人穿上了鞋。老人这才满意地笑了,说了一句著名的话:“孺子可教矣。”(这孩子可以教导了。)他让张良五天后的黎明来此地相见。
接下来的故事,更像是一场对心性的终极考验。第一次,张良天亮才到,老人已经到了,怒斥他“与长者期,后,何也?”(跟长辈约会还迟到,搞什么鬼?);第二次,张良鸡一叫就去了,结果老人又先到了,再次将他痛骂一顿。
第三次,张良学乖了,半夜就顶着寒风等在桥上。这一次,老人终于比他晚到。老人满意地从怀中掏出一本书,交给他,说:“读此则为王者师矣。”(读了这本书,你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。)这本书,就是传说中的《太公兵法》。
这段“圯上敬履”的奇遇,与其说是神仙授课,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治疗。老人用近乎羞辱的方式,磨平了张良作为贵公子的傲气和作为刺客的戾气,将他的“愤怒值”转化为了“忍耐力”和“谋略值”。从那一刻起,那个只想着用铁锤解决问题的“愤怒青年”死了,一个懂得用智慧运筹帷幄的“谋圣”新生了。
当秦末的烽火燃遍大地,脱胎换骨的张良,遇到了他命中注定的“老板”——刘邦。
在楚汉争霸的舞台上,张良不再是那个抡锤子的莽夫。他成了刘邦身边最重要的大脑。鸿门宴上,是他巧妙周旋,救了刘邦一命;楚汉对峙时,是他力主联合英布、彭越,最终垓下围歼项羽;定都关中,也是他深谋远虑的建议。刘邦后来在庆功宴上总结自己的成功时,曾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。”(“子房”是张良的字)
历史在这里,开了一个最大、也最富深意的玩笑。
那个被灭亡的、弱小的Hán国(韩),它最后的王族被杀,土地被吞并,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。然而,它最优秀的“遗产”,它那不屈的“灵魂”——张良,却以一己之力,辅佐一位平民出身的亭长,推翻了强大的秦帝国,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,最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、统一的、并且光耀后世四百年的伟大王朝——Hàn朝(汉)。
Hán(韩)的终点,竟成了Hàn(汉)的起点。同一个读音,不同的字形,却仿佛一种冥冥中的轮回与传承。
韩国的故事,从一场战战兢兢的“豪赌”开始,以一声悄无声息的叹息结束。它的一生,充满了小人物的辛酸与无奈。然而,当它的国祚终结,当它的王都被夷为郡县,这个国家最精华的部分,却在一个叫张良的青年身上,完成了涅槃。
所以,韩国真的亡了吗?或许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它用自己最杰出的一个“灵魂”,作为献给新时代的“投名状”,最终撬动了一个帝国,并以一种谁也意想不到的方式,让“Han”这个名号,以更辉煌的形式,响彻了未来的四百年。
历史,有时就是这样一出,由失败者书写最终胜利的黑色幽默剧。而那些在史书上看似被一笔带过的“小角色”,他们的故事,或许才是人性中最值得品味的部分。